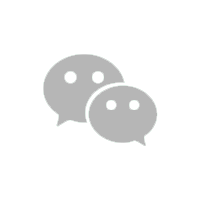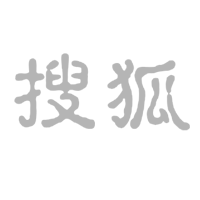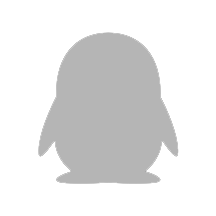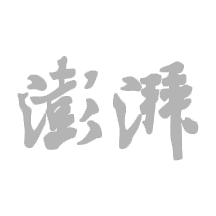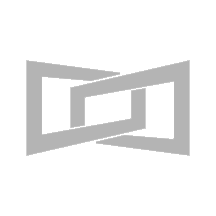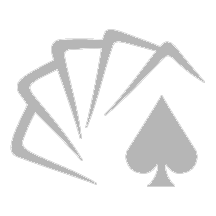通力知产 | 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使用行为认定及责任承担方式

作者 | 车小燕 王曦 通力律师事务所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是商业秘密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1两者又分别具有丰富的外延。本文聚焦于经营信息的重要子集——客户名单(或称客户信息),结合通力律师近期代理的相关商业秘密案件2,就该类信息的司法认定与责任承担问题展开探讨。纵观经济发展的历程,不管是往昔以土地和劳动力为核心的农业经济时代,还是后来凭借能源与大规模生产崛起的工业经济时代,亦或是当下这个数据驱动、创新引领的数字经济时代,客户名单始终作为企业或者商户的核心资产。尤其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借助大数据技术,客户名单所蕴含的消费偏好、行为习惯等信息,成为企业精准营销、产品创新的重要依据。近年来,随着人才流动日益频繁,涉及客户名单的商业秘密纠纷不断增多,如何依法保护客户名单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对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使用行为认定以及侵权责任承担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
一、客户名单用语变迁及法律含义
到目前为止,“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法律用语在我国的立法沿革中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3年至2007年,即我国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下称“《不正当竞争审理解释》”)施行前。这个时间段内,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尚未将客户名单明确划分到“经营信息”的范畴之下,更无进一步细化的定义,但“客户名单”的措辞已开始出现在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当时的司法实践主要是靠各地法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条文和事实的理解而在不同的案件中对涉案客户名单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作出个案认定,这些判决书中既有使用“客户名单”的,也有使用“客户信息”的,并未形成统一;第二个阶段是2007年至2020年,即《不正当竞争审理解释》施行后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下称“《商业秘密司法解释》”)施行前。《不正当竞争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在这个时间段内客户名单已被赋予准确的法律含义,属于一种特殊的客户信息;第三个阶段是2020年至2022年,即《商业秘密司法解释》施行后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9号,下称“《不正当竞争若干问题解释》”)施行前。《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三款规定:“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经营信息。前款所称的客户信息,包括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即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该司法解释将“客户名单”的措辞调整成“客户信息”,但该时间段内《不正当竞争审理解释》仍然有效,故在法律条文层面形成了“客户名单”和“客户信息”两个用语共存的情形。第四个阶段是2022年至今,《不正当竞争若干问题解释》施行后《不正当竞争审理解释》便因被取代而废止,鉴于《商业秘密司法解释》中已完成了对“客户名单”到“客户信息”的措辞调整和定义细化,故《不正当竞争若干问题解释》中并未再专门对客户名单或客户信息的问题作出规定。也即,在当前的视角下“客户信息”才是对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更为准确的法律定义。众所周知,客户名单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一个突出问题,即“客户名单”一词在公众语境和法律语境的含义分歧。在公众语境中,客户名单通常仅指简单的客户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构成的汇总信息,这种程度的客户名单基本难以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获得保护;而在法律语境中,能够构成商业秘密的客户名单则如前文提到的《不正当竞争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和《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三款等条文中描述的更加深度的信息。可能也正是为了和公众语境下的“客户名单”形成显著区分,最高人民法院才在后续的司法解释中专门将“客户名单”调整为“客户信息”。但即便如此,在如今的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当事人、律师还是法院,依然在同时使用“客户名单”和“客户信息”,这样的使用习惯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无法彻底改变。这样的现象也进一步说明了客户名单和客户信息两个不同的措辞在法律含义上并无实质区别,均指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客户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经营规律、配送方式、付款方式等3区别于公知信息且能够勾勒具体客户画像的特殊深度信息。
二、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使用行为认定
以目前最为多发的离职员工带走前雇主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类型纠纷为例,不论是在“侵权型”还是“违约型”,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要集中在不正当手段获取和使用两个行为上,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行为又进一步集中体现为“窃取”4。此类型案件的“窃取”行为通常有两种举证方式:一是从离职员工专属的工作设备中提取操作日志、外部设备插拔记录、审查邮箱或外部通讯软件使用痕迹等方式挖掘“窃取”证据;二是先证明离职员工在新公司中使用的客户名单商业秘密与前雇主客户名单商业秘密构成实质相同,从而将合法来源举证责任倒置,而这也正是客户名单商业秘密使用行为的证明重点。虽然《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已规定了认定被诉侵权信息与原告商业秘密是否构成实质相同可考虑如下五个因素:(一)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的异同程度;(二)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是否容易想到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的区别;(三)被诉侵权信息与商业秘密的用途、使用方式、目的、效果等是否具有实质性差异;(四)公有领域中与商业秘密相关信息的情况;(五)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但这里面尤其是像对客户名单类商业秘密最为重要的因素一,依然过于模糊,可操作性不足。即便如今距离《商业秘密司法解释》施行已五年,但司法实践中并无实际依据《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对原被告客户名单异同作出对比的案例,而是依然主要依靠办案法官的个人把握。
被告单纯拜访或联系客户的工作量不能构成未使用原告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有效抗辩。例如,在(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44号上海颐和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等与上海叁和商事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认为,除了2家客户外,在被告颐和公司与其余6家公司发生交易中,进行联系的业务员、交易的品种等信息均与原告叁和公司的相关经营信息构成相同或相似,且作为原告前员工的自然人被告张某了解原告此类经营信息,故可认定被告颐和公司使用了由自然人被告张某提供的属于原告叁和公司的客户信息,两被告均侵犯了原告叁和公司的商业秘密。而且,法院还认为,尽管被告与该案诉争客户之间某些具体交易的货物品种、规格与原告的交易内容稍有不同,但原被告与其客户交易的货物均为衣架、裤架等服饰辅料,两者的经营品种应属同类,因此被告构成利用原告客户名单商业秘密以不正当竞争手段与原告进行了同业竞争。该案中,作为惯常的抗辩手段,被告主张该案诉争客户名单系自己与有关客户进行过多次拜访和联系才建立了交易关系。但法院认为,对客户拜访和联系次数的多少,只是说明了被告根据有关客户名单信息与该客户落实交易所花费的工作量,并不能充分证明其如何获得该信息,不能成为否定使用他人商业秘密的理由。
被告与原告客户的定制化订单差异不能构成未使用原告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有效抗辩。在(2023)浙民再256号宁波祥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张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再审案中,法院认为,作为原告前员工的自然人被告张某离职后加入铭某公司,而铭某公司成立时间仅略早于张某从原告的离职时间,且与原告一样从事文具类外贸业务。但反常的是,铭某公司在其成立仅一年多时间内,销售到P公司、K公司的文具用品总额已高达220余万美元。鉴于P公司、K公司均系张某建立的联系,并负责接待,交易模式及交易流程和原告公司与该两客户的模式、流程实质性相同,标的同为文具类产品,部分对方具体联系人还系张某在原告公司曾有过联系的人员,足以认定张某使用了与该案诉争信息实质性相同的信息。该案中,作为另一种常见的釜底抽薪式抗辩手段,被告主张虽然其客户名单与原告重合,但P公司采购的文具系定制产品,每次需求内容不同,因此对后续交易的达成没有价值。对此,法院认为,虽然每次定制的具体设计需求有所不同,但联系方式、同类产品报价、具体交易方式乃至产品设计风格等内容仍具有一定稳定性,故产品是否系定制并不影响涉案经营信息具有商业价值的认定,该些经营信息能够为使用者带来竞争优势,故同样不能成为否定使用他人商业秘密的理由。
被控客户名单与权利人客户名单重合比例对使用行为认定的影响。在(2018)最高法民申1273号宋某与鹤壁睿明特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自然人被告宋某,一、二审已查明其在原告反光材料公司工作期间擅自通过多家物流公司向东北地区发送货物18次,货物品名与反光材料相关或类似,且交易的客户名单与反光材料公司的客户名单有重复,存在擅自与原告反光材料公司的客户进行交易的行为,构成对反光材料公司商业秘密的侵犯。虽然宋某交易的客户与反光材料公司的客户名单重复的仅有董显远,但并不影响其侵权行为的构成;而对于另一被告睿明特公司,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睿明特公司与东北地区交易客户中与反光材料公司交易客户相重复的客户有6户,据此可以认定睿明特公司所使用的客户信息与反光材料公司的经营信息存在相同或实质性相同的特征。这说明之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控客户名单与权利人客户名单重合比例的大小并不影响实质性相同特征或使用行为的认定。但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670号沈阳博某实业有限公司、博某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等与沈阳高某炉料有限公司、沈阳熹某冶金炉料有限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及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却相反地认为,经过比对,被告被诉侵权软件系统数据库中仅有20家客户信息与原告信息实质性相同,仅占原告441家客户信息的4.5%,且原告自称有2万多家客户信息,虽然被告在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时拒绝配合,且亦不能排除被告存在删改客户信息的可能性,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进行同一性比对的被告客户信息存在严重删改的情形,故在没有足以推翻上述认定的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对于4.5%的同一性比对结果予以采信。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使用的客户信息与原告主张权利的客户信息构成实质性相同,未完成初步证明,故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很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670号案中的观点与其在(2018)最高法民申1273号案中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180度大转弯。虽然无法参透最高人民法院在前述两起案件中持自相矛盾的司法观点的真实原因,但笔者管见以为,即便现在有(2022)最高法知民终670号案作为新的司法指引,但该案并未覆盖已有明确证据、确凿证明离职员工窃取前雇主客户名单商业秘密并入职新公司后的使用情形。即,如果原告已充分举证证明离职员工窃取了原告构成商业秘密的客户名单(例如将原告客户名单擅自发往私人邮箱或通讯软件账户等),且亦已穷尽所能举证证明被告(即离职员工入职的新公司)在短时间内与原告老客户建立联系并开始交易,即便此时原告仅能主张被告客户与原告客户名单存在个别重合,但鉴于原告举证被告完整客户名单的极高难度,以及原被告客户发生重合等事实发生于离职员工的窃取行为之后,故应推定被告的其他客户名单与原告客户名单构成实质相同,将重合比例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一旦被告举证不能,则应由被告承担不利后果。如此,才能实现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中原被告利益的平衡。
客户名单实质相同的刑事视角借鉴。时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副检察长谈信友和检察官潘莉曾在发表于《检察日报》的《办案要务大家谈|“四步法”认定客户信息是否属于经营信息》一文中总结,“只要与权利人原先客户(这些客户信息是明显不同于公开领域中的一般客户资料,是属于特殊需求的深度信息)从事了类似产品交易,则应视为是实质性相似。如:犯罪嫌疑人曾与权利人客户进行联系并就原有产品的用途、效果、价格等内容磋商的证据;权利人收到的来自客户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要求降价邮件;权利人原客户突然另寻新上家且新上家与权利人曾有过交集的,权利人市场份额存在被同行业侵占市场风险等。” 笔者管见以为,基于基本的法理,如果该文提到的前述情形都足以被认定为更严重的刑事意义上的实质相同,那么类似情形在民事诉讼纠纷中便更应作出有利于权利人的认定。
三、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责任承担方式
《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了商业秘密纠纷停止侵权的具体方式,“人民法院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判决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时,停止侵害的时间一般应当持续到该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时为止。依照前款规定判决停止侵害的时间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依法保护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判决侵权人在一定期限或者范围内停止使用该商业秘密。”该条款的核心思想在于亡羊补牢,以尽可能减小权利人的进一步损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纠纷的责任承担方式并非仅仅是单一的停止侵权,而是大致分为如下三种方式。
方式一:仅赔偿经济损失,不支持停止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312号香港某开发公司与魏某乙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认为,“与普通民事侵权案件中的停止侵害责任不同,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的停止侵害民事责任通常需要设定期限。尤其是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其不同于技术秘密,客户名单的载体通常不会通过销售等方式公之于众,要求被诉侵权人停止侵害的时间持续到公众知悉时,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与客户名单无限期保护,是对交易自由的不合理限制,不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并且,客户名单中所包含的客户交易习惯、意向、价格等信息,他人亦可以通过花费时间和投入等正当手段从公共领域合法获得,禁止侵害该经营秘密的核心在于禁止侵权人利用该经营秘密作为‘跳板’损害权利人的竞争优势。因此,判决停止侵害经营秘密时,应考虑该经营秘密领先优势的可能持续时间。如果被诉侵权人已经离开原单位较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客户信息的价值和带来的竞争优势已经明显减弱甚至消失,那么再判决其停止与客户名单中的客户进行交易就失去了必要性和时效性。本案中,魏某乙自2011年12月从香港某开发公司辞职,开始运营香港某科技公司、深圳某科技公司至今已十年有余,而香港某开发公司所主张的客户名单信息系形成于魏某乙离职之前,在此十余年期间,客户名单中所包含的客户交易习惯、意向、价格等信息带来的竞争优势早已减弱甚至消失,再限制香港某科技公司、深圳某科技公司停止与相关客户名单中的客户进行交易既无必要,也不合理,故对香港某开发公司要求停止侵害的主张,本院不再支持。”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商业秘密案件停止侵权的核心在于禁止侵权人利用该经营秘密作为“跳板”损害权利人的竞争优势,故一旦对簿公堂的时间与侵权行为发生时间间隔过于久远,法院便可能认为涉案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竞争优势已明显减弱或消失,从而不再支持停止侵权的主张,并仅判决赔偿损失。该案体现出的司法倾向无疑也警醒着权利人应及时维权。
方式二:仅笼统支持停止侵权,但未明确具体方式。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4)粤0604民初17535号佛山某有限公司、凯朗某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法院的停止侵权判项为“被告潘某、曹某、佛山某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3)浙02民终1470号宁波渠成进出口有限公司、邬天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中,法院的停止侵权判项同样为类似的“被告邬某、周某、宁波印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宁波渠成进出口有限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即停止使用涉案原告的客户信息”。上述两起案件虽均发生在《商业秘密司法解释》施行后,但仍是笼统判决停止侵权或停止使用原告客户信息,而未对停止的方式或者期限、范围等作更加细致的区分,故此类案件在实操中并无多大参考意义。
方式三:禁止被告在一定时间段内与原告客户开展相关业务。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案中审理的(2020)京73民终2215号康哲等与北京霍兰德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法院判决“康某、湖南汇百亿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北京霍兰德贸易有限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即在两年内停止披露、使用北京霍兰德贸易有限公司的涉案14家客户信息(包括客户名称、联系方式、联系人及客户需求,给客户的报价等,详见附件),在两年内停止与北京霍兰德贸易有限公司的涉案14家客户进行磋商及交易”,以及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闽民终1140号徐陆平、厦门会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法院亦判决“徐某、厦门会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厦门三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不得与厦门金牌橱柜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独辫子服饰有限公司从事与厦门三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有竞争性的业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7)闽民终1140号虽然在《商业秘密司法解释》施行前,但法院仍充分考虑了客户名单商业秘密的竞争优势与时间的关系,为禁止被告与原告客户开展竞争性业务划下了一个合理的期限;而(2020)京73民终2215号案除了划下期限外,还对停止披露和使用的客户信息界定了更加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范围。
结 语
客户名单作为企业核心商业资产,其司法保护始终处于立法与裁判实践的动态调适之中。从“客户名单”到“客户信息”的用语演进,不仅体现出法律对客户信息保护要求的深化,更凸显司法机关对信息结构与深度价值的日益重视。在侵权认定方面,虽然过往的审判经验中早已摸索出“实质相同”的判断标准,且后来还有《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十三条作为补充,但该规定所提出的因素仍显原则化,司法实践中继续依赖于办案法官的个人内心倾向,尚未形成清晰、可操作性强的统一标准。在责任承担方面,《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则体现了更具平衡感的司法理念,强调在保护权利人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应合理考量时间因素与市场竞争自由,避免对客户信息予以无限期保护。
注释
1. 《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修订)第十条(旧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2. (2025)粤03民初3576号。
3. 《人民法院案例选》2016年第3辑。
4. 法条原文为“盗窃”,本文此处使用更偏向实操中更常使用的“窃取”一词。
联系作者

车小燕
通力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cherri.che@llinkslaw.com

王曦
通力律师事务所 业务律师
wonssi.wang@llinkslaw.com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编辑 | 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