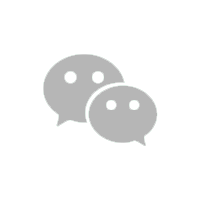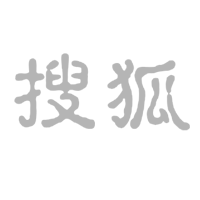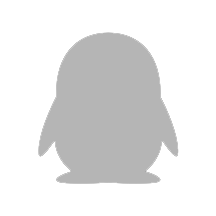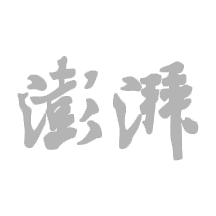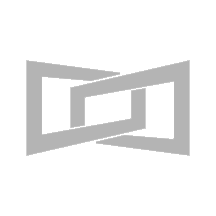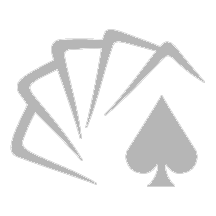ZY正见 | 刷单行为怎么看

作者 | 张诗雨 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
编辑 | 布鲁斯
随着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崛起,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了主流的消费方式。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权利人也往往通过被告侵权产品的网上销量去计算侵权人的获利,进而主张相应的赔偿额。然而,实践中却屡次出现被告通过主张自己的侵权产品存在刷单情形来对原告主张的较高赔偿额进行抗辩。这一现象为权利人的有效维权、筛选侵权目标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与迷惑。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的动态对刷单行为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赔偿额计算中的态度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刷单是什么?
刷单,一般是指电商商家通过制造虚假销量、商品评价等信息以获得竞争优势地位的行为。其目的是通过虚构的销量及评价在电商平台上获得更高的权重从而拥有更高的浏览量、误导消费者基于虚假的销量及评价而购买该商家的商品,或是通过相反的手段来打击竞争对手。从司法实践中披露的规模性刷单来看,刷单组织的收费根据内容的不同从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
二、法院如何看待刷单行为?
实践中,不同的法院对刷单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将法院的观点分为以下三类:
观点1
刷单形成的销量应当被扣除在赔偿额的计算之外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苏民终160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刷单所形成的销量不能被作为真实交易数据对待”,最后,法院通过考量了被告实际可能的销售额及获利、原告商标知名度等因素后适用了法定赔偿。[1]江苏省高院对于刷单行为的不法性未作评述,但根据其关于确定判赔额的论述可以看出,该院将刷单所形成的销量剔除于赔偿额的计算与考量之外。
与之观点相似的是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六,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知识产权案件赔偿额的确定仍然是需要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的销量情况。因此,若法院查明相关交易数量系刷单而来,则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予以扣除”。[2]
可以看出,前述法院均认为,在可以确认被告的部分销量系刷单形成的情况下,应当在确定赔偿额时予以扣除。
观点2
刷单证据应当严格审核
部分法院则更进一步,确认了刷单行为对诚实信用原则和合法经营理念的违背,在审查刷单证据时采用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即只有当相关证据足以形成闭环链条且可以相互作证时,才应当将刷单部分的销量予以剔除。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2020年度深圳法院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之十中,确认了刷单行为的不法性,“‘刷单’作为灰色产业一环,损害了平台的交易统计机制和信用评级机制,属不诚信经营行为”,深圳市中院和福田区法院也均认为:“对销售商提供的‘刷单’证据应当严格审核,只有在交易记录、付款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形成闭环链条且可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方可对该部分销售数量予以剔除。”[3]深圳法院对于刷单抗辩较为严格的审核标准,也为权利人对被告刷单证据的成功质证提供了较高的可能。
北京互联网法院的观点与之类似,认为:“刷单形成的虚假交易量,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合法经营理念,不应被鼓励和提倡。被告在选择刷单方式牟取不当利益的同时,亦应承担其可能产生的商业风险和法律责任。在无法查明实际销量的情况下,刷单部分的销量不应予以扣除,法院将其计入侵权赔偿数额。”[4]从反面来说,在能够查明实际销量的情况下,应当将刷单部分扣除。
观点3
刷单形成的销量不应当被扣除在赔偿额的计算之外
笔者注意到,也有部分法院对于刷单,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态度,即认为刷单不应当作为侵权人免责的正当理由。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刷单行为虽然使侵权人实际侵权获利相对减少,但是该行为依然对商标权利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使得权利人商品的市场营销、商品商誉、市场份额受到不利影响和冲击,因此,刷单行为不能成为侵权人免除赔偿责任的正当理由。”[5]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样对刷单行为持否定性的评价,认为将网店标明的销售数量作为确定赔偿额的参考因素,有利于引导市场主体规范经营和诚信经营,并且最终确定的法定赔偿数额应较其他未刷单侵权人更高。[6]
三、笔者观点
笔者更加赞同第3种观点,即刷单形成的销量不应当被扣除在赔偿额的计算之外,并且相对于其他未刷单的侵权人,刷单的侵权人的赔偿数额应当更高。笔者认为,即便不能适用第3种观点,至少也应当适用第2点,对证明销量系刷单形成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核。而这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刷单行为是一种危害多方利益的行为,不利于诚实信用、公开透明的网络购物环境的建立;第二,若将刷单数据排除在赔偿额的考量之外,将不利于公平公正的诉讼环境的建立。具体而言:
(一)刷单的危害辐射电子商务环境中的多方主体
1. 使知识产权人维权困难
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侵权人可能会通过主张涉案商品的销量系刷单的结果而企图降低赔偿额。实践中,部分法院也的确会将侵权人的刷单行为排除在赔偿额的考量之中(如江苏省高院和嘉兴市中院),即在被告能够证明特定部分的销量系通过刷单所得时,法院会将此部分销量扣除在赔偿额的考量范围之外,以实际的交易数量来计算赔偿额,或是视为无法查明被告获利及原告损失而适用法定赔偿。
因此,刷单行为会为权利人确定赔偿额、赔偿额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带来困难。不仅如此,权利人在前期筛选侵权目标时,也往往会通过相关产品的销量确定诉讼目标,若权利人被侵权产品虚高的销量误导,在前期投入了大量的维权成本,但最终却因被告刷单而仅能获得少量赔偿,这将在极大程度上打击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造成权利人的二次损失。而反观侵权人,刷单不仅为其增加了本不属于它的竞争优势与交易机会,甚至还可以让其在此种行为被权利人发现并采取维权行动后,以“刷单”为由抗辩权利人主张的赔偿额,从而逃脱法律的惩罚。如此,在权利人进退两难之时,侵权人却进退自如。
2. 使知识产权人及其他同业经营者商业利益受损
一方面,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产品通过刷单获取了本应归属于知识产权人的较高流量与商誉,同时,因产品宣传与实际情况的出入而带来的商誉降低的后果却很可能被加在了知识产权人的头上。这使得知识产权人不仅被抢走了原本的市场份额,还面临着声誉无端受到损害的后果。另一方面,在消费者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刷单商家凭借虚假数据所获得的较高流量与商誉也势必会减弱甚至剥夺消费者对其他同业经营者的注意,这同样将使得其他诚信经营者的商业利益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损害。
3. 危害公平、透明、诚信的电子商业环境
从整个商业环境来看,消费者知情、电商商家公平竞争、电商平台以信用评价体系引导及管理等环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电子商务生态环境。而电商商家的刷单行为,干扰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基于虚假的销售数据和用户评价不正当地获得了竞争优势和交易机会,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提高了电商平台维护电商生态的经营成本,降低了消费者对电商评价体系的信任,从长远看,彻底打破了多方共同营造的公平、透明、诚信的电子商业环境,可谓百害而无一益。
(二)若将刷单数据排除在赔偿额的考量之外,将不利于公平公正的诉讼环境的建立
若被告不仅能通过刷单行为获取不法的竞争优势和交易机会,还能通过此种不法行为进行抗辩而在诉讼中获得诉讼优势,这将使刷单行为演变成一种只为被告带来收益,而不会让其因此而受到惩罚或损失的不法行为,如此明显的不公平将严重打击权利人的维权积极性,不利于公平公正的诉讼环境的建立。从长远来看,这种双重获利将鼓励被告及其他市场主体更多地参与到刷单行为之中,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笔者认为,在涉及刷单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赔偿额的计算不应仅仅考虑权利人的直接经济损失,而应当综合考虑刷单行为带来的不利后果,将其纳入赔偿额的考量范围之内,相对于其他未刷单的侵权人,刷单的侵权人的赔偿数额应当更高。特别是,在大多数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均无法准确计算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的情况下,刷单行为所形成的销量更应当在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时予以充分考量,即便部分法院认为不应将此部分虚假交易的数据算作被告可能的获利,但刷单行为仍可以被视作被告主观恶意的表现形式之一,而被纳入赔偿额的考量之中,而这一点正是因为相较于前者,后者在侵权行为中的恶意与负面影响更大。
即便不采取第3种观点的做法,司法实践也应考虑适用第2种观点。对于实施了刷单行为的被告来说,提供足以形成闭环链条且可以相互作证的刷单证据并非难事,被告实施刷单的交易记录、付款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实际上并不需要被告耗费多大的努力才能获得,在此种情况下,对被告的刷单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在实际上并未给被告增添举证负担。正相反,若允许被告仅凭一句“销量系刷单而得”的抗辩就足以对抗权利人主张的赔偿额,反倒为权利人增加了举证的负担。诚然,将刷单数据排除在赔偿额的考量之外的做法的确遵循了民事赔偿的填平原则,但考虑到刷单行为给电子商务环境以及公平公正的诉讼环境带来的损害,法院应当对其予以否定性的评价,并在司法实践中尽力遏抑刷单行为的猖獗。
四、结 语
刷单是一种危害后果辐射多方的不法行为,若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允许被告通过这种不法行为而获得较为乐观的诉讼结果,这将放纵刷单行为肆意发展,愈演愈烈,不利于良好网购生态的建立。因此,如果司法实践能够对刷单采取较为严厉的裁判标准,或者在判赔额上对刷单商家施以更高赔额,或者对于刷单证据予以更为严格的审查,将对于维护公开、透明、真实、公平的市场秩序与诉讼环境有更好的推动作用。
注释
[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终1609号民事判决书。
[2]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六。
[3]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4027号民事判决书。
[4]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2020年北京互联网法院涉网著作权八大典型案例之七,(2019)京0491民初21102号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公司诉张某某侵害美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
[5]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1)沪73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
[6]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9年度湖南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件之六,(2019)湘民终 97 号上诉人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胡海燕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联系作者

张诗雨
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
shiyu.zhang@zypartners.com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