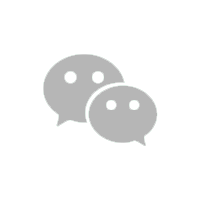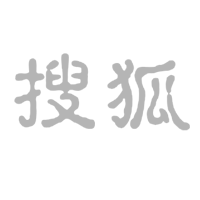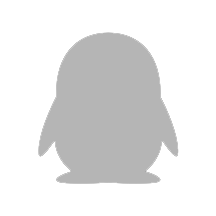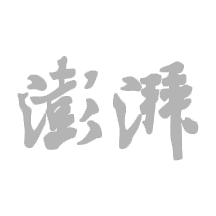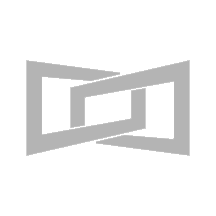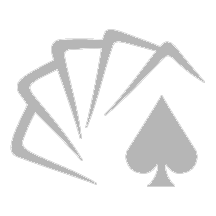特稿 | 扩张后的广播权对互联网音乐行业的影响
作者 | 王飞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编辑 | 布鲁斯
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新《著作权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为适应网络直播、同步转播使用作品等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新著作权法》对广播权有关表述进行修改,扩张了广播权的定义,使之能够控制网络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新广播权的扩张将对以网络直播表演为主要营收的互联网音乐行业影响深远,而录音制作者被赋予广播获酬权将进一步推动互联网音乐行业与音乐集体管理组织合作变革。
一、 扩张广播权的合理性
(一) 原广播权的局限性
参与《著作权法》立法工作的亲历者指出,原《著作权法》对于广播权的规定“是为了执行《伯尔尼公约》,与公约保持一致”[1]。该文本直接来源于《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之二第1款的规定。
1.原广播权仅可控制“初始无线传播”
《伯尔尼公约》虽未对“广播”进行定义解释,但通过其将“广播”(broadcasting)与“以任何其他无线传送符号、声音或图像的方法向公众传播”(by any other means of wireless diffusion of signs, sounds or images)并列可以看出,广播是“无线传送的方法”之一,其含义是指“以无线的方法传播”。其他国际条约亦作出类似规定,例如,《罗马公约》第三条第(f)款规定,“广播”是指供公众接收的声音或图像和声音的无线电传播[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三条第(f)款规定,“广播”系指以无线方式的播送,使公众能接收声音、或图象和声音、或图象和声音表现物[4]。
参与《著作权法》立法工作的亲历者指出“直接以有线方式传播作品”可以为第十条第1款第17项的“其他权利”所包括[5],原广播权定义不包括直接以有线方式进行的传播。无论是《伯尔尼公约》,还是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均只控制三种行为,第一种为“以无线方式传播作品”。[6]从初始广播信号的性质看,由《伯尔尼公约》规定的广播权体系基本包括无线广播权,它所规范的广播信号仅为“初始无线广播信号”。[7]由此,原广播权控制的第一种“广播”行为是“无线传播”,“有线传播”未纳入控制范围,原广播权控制的第二种行为和第三种行为的宾语“广播的作品”仅是指“通过无线方式传播的作品”。
广播权控制三种对作品的广播行为,分别为:无线广播、对广播的转播,以及公开播放接收到的广播[8]。限于缔约时的技术环境,《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有线广播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其只包括以有线传播或转播广播作品的情况,直接进行的有线广播并不在此限[9]。所以,原广播权控制的三种行为局限于:(1)以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2)接收到原广播机构包含作品的无线信号后,再以无线或有线方式将其同步向公众转播;(3)接收到原广播机构包含作品的无线信号后,再通过扩音器、电视等设备或手段将其向公众播放。
2.原广播权控制范围局限导致法律适用混乱和争议
根据原广播权条款,作者只对“广播的作品”才享有“广播权”;而如果某一作品之前没有被广播,则在直接有线传播该作品时,作者将无法享有“广播权”[10]。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如果初始传播采用“无线”方式,相关转播行为即属于广播权调整范围,但是如果初始传播采用“有线”方式,则转播行为就不属于广播范围,而应属于“其他权利”所规范的行为[1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指出,如果根据初始信号属无线或有线而分别适用广播权或“其他权利”,势必会增加原告举证负担,并且法院对初始有线信号该如何保护没有提出彻底的解决方案,从而可能引起更大分歧。[12]由此,无论是针对无线广播作品实施的网络实时转播行为,还是针对网络直播作品实施的网络实时转播行为,均应依据“其他权利”进行规制。[13]正是原广播权仅控制初始无线传播的局限性,导致转播初始有线传播行为具有不同的法律定性,而直接以有线方式进行的非交互式传播亦无法落入广播权的控制范围,违背“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
(二) 通过扩张广播权解决原广播权局限更合理
为解决我国“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法律定性问题,有学者建议用“播送权”代替“广播权”以使其能够覆盖和控制更多的播送行为[14];有学者主张扩张“广播权”的定义,使之能够控制各种“非交互式”的传播行为[15];也有学者提出用“公开传播权”重组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以及无线传播权、有线或无线转播权以及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16]。广播权的修改经历了从2014年送审稿以“播放权”[17]代替到2020年审议稿扩张广播权定义的过程,而以扩张广播权控制范围的方式来调整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更加合理。
1.扩张广播权符合“技术中立”立法原则
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交互式”传播相对应,广播权控制的行为是公众需按照传播者安排的时间获得传播者提供的作品,例如公众只能按照电视台指定的节目时间观看节目,而不能选择时间和内容,是一种“非交互式”传播。而在新型的网络直播、网络实时转播、网络定时播放等,同样只能即时欣赏系统按照既定的节目时间表正在播放的节目,其效果相当于打开电视机,在某一频道中收看电视台正在播放的电视节目,只是传输终端从电视机变成了电脑而已[18]。无论传播是通过无线还是有线,“无线或有线”仅是技术手段,其传播特征和后果完全一致。由此,无线传播和有线传播的法律定性应当相同,而不应发生无线传播受广播权规制、有线传播受“其他权利”规制的局面。相应地,在原《著作权法》广播权规制无线“非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交互式”传播的已有体例下,进而将有线“非交互式”传播纳入广播权控制范围,符合“技术中立”立法原则。
2.扩张广播权保持著作权法逻辑统一
为弥补《伯尔尼公约》缺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作为《伯尔尼公约》的特别协议,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机械表演权、广播或无线传播、对广播的有线转播或无线转播、机械朗诵权、电影的公开放映权和有线公开传播权等权利的情况下[19],扩展规定用户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通过行使这些权利传播的作品[20]。WCT第8条前半段规定了广泛的“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的权利”(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后半段明确列举指出通过网络进行的“交互式”传播受“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控制。WCT第8条后半段也就是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原广播权源于《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之二第1款,而WCT第8条是针对《伯尔尼公约》缺陷进行弥补,使得“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可控制任何“以有线或无线方式”传播的行为。2001年我国《著作权法》修改借鉴了WCT第8条后半段增加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未吸收WCT第8条前半段规定广泛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而是保留了《伯尔尼公约》的狭义广播权,导致原广播权仅能控制初始无线传播,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和争议。由此,由于WCT第8条拓展了《伯尔尼公约》中传播权的范围,我国作为WCT的缔约方,完全可以根据WCT重新对“广播权”的定义进行合理解释[21]。2020年《著作权法》修改即是将WCT第8条前半段进行吸收,扩张广播权的定义,特别是本次修改借鉴WCT第8条“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机械表演权、广播或无线传播…等权利”的前提,保持我国《著作权法》原表演权、放映权规定不变,保证广播权的扩张不会与表演权、放映权适用冲突,同时通过“但不包括本款第十二项规定的权利”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区分。该修改方式既保证著作权法体例修改最小,也保持与国际条约法律逻辑的一致,更加具有合理性。
新《著作权法》将广播权进行扩张,不再局限于控制“初始无线传播”,而是能够控制“以有线或无线”的各种非“交互式”传播行为,将网络直播、网络实时转播、网络定时播放等纳入控制范围,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
二、 新广播权理解适用的两个问题
(一)“广播的作品”应当做扩大解释
新广播权后半部分未修改原广播权控制的第三种行为的规定,即“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而新广播权前半部分规定没有再使用“广播”二字,从“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修改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由此,涉及广播权规制的“通过扩音器等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行为时就需要对“广播的作品”进行解释。
鉴于原广播权是建立在初始的无线广播的基础之上,“公开播放广播”并不能控制他人公开播放那些通过有线方式传播的节目[22]。由此,原广播权控制的第三种行为公开播放“广播的作品”是指再次公开播放接收到的通过无线方式传播的作品。而《著作权法》对新广播权的定义进行扩张,使其规制任何有线和无线方式传播,相应地应当对“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中“广播的作品”进行扩大解释,此处“广播的作品”应包括初始信号是有线或无线传播的作品。
如果仍依照原“广播”是“无线方式传播”的狭窄定义,将会在适用“通过扩音器等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规定时再次出现类似体育赛事转播案的困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凤凰网赛事转播案”指出,对于以有线方式直接传播作品的行为或者网络直播初始信号来源不是广播的作品的行为,由于不存在初始广播行为,故不属于广播权控制的行为,只能适用“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予以调整,从而出现相同类型的直播行为仅因初始信号来源不同而适用不同权利进行调整的局面。[23]。例如,互联网平台通过有线网络直播跨年晚会,商场接收到晚会直播信号后通过电视机直接在营业场所向公众播放。针对商场“公开播放跨年晚会”的行为,由于跨年晚会初始信号是有线方式传播,如果不对“广播的作品”做扩大解释,将无法适用新广播权规制,而只能适用“其他权利”调整,导致再次出现仅因初始信号来源不同而适用不同权利进行调整的局面。
(二)广播权与表演权的区别在于是否向不在传播发生地的公众传播
新《著作权法》并未修改原表演权的内容,由此表演权规制的“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行为将与新广播权规制的以“有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表演的范围之间产生重叠。事实上,原广播权主要控制三种行为:以“无线”方式传播作品;以“有线”方式转播作品;以“扩音器或者其他类似工具”传播作品。从文义上解释,这三种传播方式完全可以被包括在机械表演权的“各种手段”之中,从而造成机械表演权与广播权的交叉重合。[24]参与立法的工作者也指出“使用有线广播传送作品属于机械表演”[25]、“表演权中的‘机械表演’可以涵盖面向公众‘将现场表演用转播设备直接进行有线播放’的行为”[26]。进而学者也提出“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地方接收广播或有线传播的作品及其录制品的行为也属于机械表演”[27]、“严格来说,放映权属于机械表演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设备来表演美术、摄影和电影作品。”[28]
虽然我国机械表演权的国际法源是《伯尔尼公约》第11条第1款第(2)规定的“授权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其作品的表演和演奏”[29],但参与立法者对表演权的解释是“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指的是‘机械表演’,机械表演指借助录音机、录像机等技术设备将前述表演公开传播。”[30]说明立法者并没有意图将那些向不在现场的受众传播作品的表演的行为纳入《著作权法》中表演权的控制范围。因此,虽然《著作权法》对表演权的定义与《伯尔尼公约》相近,但其含义存在实质性差异。[31]
实际上,《伯尔尼公约》的起草者倾向于希望将在公众中表演作品的行为与将作品(或者作品的表演或朗诵)向不在传输发生地的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加以区分[32]。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表演权”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为并列关系,不能控制广播行为和网络传播行为[33]。之所以将“有线或者无线公开传播”解释为向不在传播发生地的公众进行的传播,是因为在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及《著作权法》中,凡是以“有线或者无线”作为限定的传播,都是指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向不在传播发生地的公众进行的传播[34]。在我国《著作权法》已经单独规定广播权的情形下,显然“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不能再规制“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表演的行为。相应地,新广播权已经明确将以“有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表演纳入规制范围,“表演权”的涵盖范围亦不应当与之相重叠。
从本质上来讲,理解《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权,只有抓住了表演的根本性特征——在特定范围内发生的传播[35],“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不包括向不在现场的公众进行传播[36]。而广播权所控制的广播行为,能够让不在现场的公众或者社会公众成员都能获取作品[37]。由此,表演权与广播权的界定是是否向传播发生地外进行传播,表演权仅包括向现场的公众进行播放的行为,而不包含向传播发生地之外的公众传播的行为[38]。进而,直接用扩音器之类工具公开播放作品的表演属于表演权规制范围,而用扩音器播放接收到的信号(无论初始传播信号是有线或无线)则应纳入广播权规制范围。所以,营业场所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播放背景音乐因侵犯表演权需支付版权许可费,播放有线或无线广播节目因侵犯广播权亦需要支付版权许可费。
三、 新广播权对互联网音乐行业的影响
(一) 新广播权将左右互联网音乐平台发展
1.新广播权将成为音乐直播行业最核心的授权项
根据艾瑞咨询《2020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数字篇》显示,2020年音乐直播用户月活超3亿,预计2022年中国音乐直播市场规模将超1000亿元[39]。鉴于原广播权局限于初始无线信号范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游戏直播行为列入“其他权利”的规制范围[40]。北京互联网法院将直播表演唱歌行为纳入“其他权利”规制范围[41],亦从法理层面否定表演权规制直播表演唱歌。而广播权本次扩张后将可规制非交互式的无线或有线传播,直接产生网络直播纳入新广播权规制范围的法律效果。
在此前直播表演唱歌行为未定性前,音乐直播平台与版权方或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音著协”)授权合作中,一般是将直播唱歌作为单独使用场景或笼统归入信息网络传播权中进行授权约定。广播权本次扩张,一方面网络直播行为将明确纳入广播权规制范围,进行音乐直播(包括自弹自唱、清唱、使用原唱伴奏演唱、播放音乐作为背景音乐等)需明确取得词曲广播权的授权;另一方面,鉴于直播仅是广播权扩张后规制行为的一部分内容,对于网络直播平台而言,需要与版权方、音著协进行新的授权协议洽谈,协议需明确涉及到网络直播的广播权授权范围和使用场景,明确限于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在直播平台开设直播间进行直播传播,包括接收初始信号再传播,但不包括传统广播电台传播、网络电台传播、定时播放等行为。此外,类似于传统音乐广播电台的互联网音乐电台也正在崛起和蓬勃发展,此类通过有线非交互式方式传播音乐作品的行为同样也将受扩张后广播权规制。无疑,本次广播权扩张对于互联网音乐行业授权合规是新的挑战,使得广播权成为音乐直播行业最为核心的授权项。
2.录音制品制作者广播获酬权将加剧行业竞争
新《著作权法》响应音乐行业呼声,赋予录音制作者广播获酬权。新《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有线或者无线公开传播”实际就是新广播权定义的一部分。而新广播权规制范围已经扩张到网络直播领域,由此,对于音乐直播而言,直播直接播放音乐(录音制品)、直播表演唱歌使用原唱伴奏(录音伴奏)、直播(不限于音乐直播)过程中播放音乐作为背景音乐等,除取得词曲广播权的授权外,还需向录音制作者支付报酬,录音制作者权利保护得到完善。因此,对于音乐直播而言,需同时取得词曲广播权、录音制品广播权的授权,如提供回看功能的还需取得相应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词曲、录音制品版权支出将成为音乐直播平台的重要支出之一,音乐直播行业竞争将加剧。本文建议,对于音乐直播平台而言,可通过版权授权、版权收购、创建互联网音乐平台自有厂牌、培养平台独立音乐人等形式保证在线音乐、社交娱乐服务合规化。
伴随传播技术的发展,音乐著作权已是著作权领域内最复杂的制度体系,其权利主体众多,权利类型复杂,权利客体分立,导致音乐著作权制度运作成本逐步上升[42],而广播权的扩张将使得音乐版权授权更为复杂。受疫情影响,直播现场音乐演唱会成为全球趋势,复杂情形下,互联网音乐平台直播现场演唱会,要取得词曲现场表演权、词曲广播权、词曲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还需要向录音制作者支付广播权报酬和机械表演权报酬,取得录音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广播权扩张不意味着广播组织法定许可的扩张
新《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因新广播权从仅控制“初始无线传播”到控制任何无线和有线形式的传播,部分观点提出,新《著作权法》施行后,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过网站定时传播、实时转播和网络直播使用已发表的音乐作品,无需经权利人同意。[43]但是,即使广播权获得扩张的情形下,广播电台、电视台获得的法定许可显然不能够扩张适用到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网站。
第一,邻接权是绝对权,必须由法律加以清楚、明确地界定。对于著作权,避免因立法的滞后和术语的过时而导致对作品的新型利用方式无法受到著作权人的控制,《著作权法》为著作权人提供了“其他权利”的兜底保护。而对于邻接权,《著作权法》并未规定“其他权利”。显然,立法者无意为包括广播组织权在内的邻接权留下拓展保护范围的空间。[44]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八条[45]和《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第三条[46]定义,结合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广播组织权的立法背景和各国的立法例,可以认为,在我国能够享有“广播组织权”的广播组织为“无线广播组织”和“有线广播组织”,但不包括“网播组织”。[47]在进入“三网合一”时代后法定许可规则已不再具有正当性,因此建议在未来立法修改时废除对广播电视组织初始广播给予广播权法定许可的规定[48]。在未有明确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界定“播放”一词包括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进行播放的情形下,广播组织通过网站形式进行的定时传播、实时转播和网络直播,显然不属于法定许可的范畴。
第二,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网络电视台进行初始广播是不能适用权利限制规则的。如果广播电视组织同时办理网络电视台,就会出现同一家机构因为其传播媒体的不同而在相同的传播内容上适用不同的规则。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广播电视组织进行比较,前者的收费标准远远低于后者,但却承担了比后者更多的义务,这也不利于网络数字媒介的发展。[49]广播组织的网站与互联网音乐平台本质无任何差异,通过扩张解释法定许可主体而赋予广播组织网站法定许可,这对于互联网音乐平台显失公允。
最后,过往国家基于政策引导和扶持赋予公益性广播组织法定许可具有一定时代背景,而现今广播组织多以营利为目标且已全面进入互联网领域。对于权利人而言,互联网已成为作品传播的最核心渠道,在广播权扩张的前提下就直接将法定许可主体扩张到广播组织的网站,权利人失去在互联网传播领域自愿许可和交易的谈判机会,这将对权利人利益造成极大损害,也将对已建立的互联网音乐版权市场秩序造成破坏性冲击。
(三)新广播权将加速音乐集体管理组织改革
1.新词曲广播权应继续由音著协管理
原词曲广播权(电视台、广播台使用支付报酬)、词曲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音乐平台、直播平台、手机App应用商等使用支付报酬)由音著协统一管理和发放许可。根据音著协年报显示,2020年词曲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收入2.216亿元,词曲广播权许可收入4542万元[50]。在音著协与互联网平台达成的合作授权协议中,网络直播涉及的词曲授权一般会笼统地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场景中进行约定。
广播权扩张后,直播表演唱歌、直播播放音乐作为背景音乐、网络电台定时播放歌曲、直播或实时转播演唱会等均需取得词曲广播权许可,由音著协基于此前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管理和收费经验继续管理和发放许可符合版权市场交易习惯,更加合理和顺畅。
广播权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音著协权限进一步扩张。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类作品通常只存在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这样,无形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事实上处于一种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对于著作权保护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是也存在滋生官僚主义、滥用职权的潜在危险[51]。在此方面,新《著作权法》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作出更细化的规定,推动集体管理组织建立更为公开化、透明化的制度,逐步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公信力,以鼓励音乐人、权利人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2.录音制作者互联网广播获酬权不适宜由音集协管理
部分学者在建议赋予录音制作者广播权和表演权的同时,也提出,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广播权、表演权、出租权应当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52]。但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加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自愿为基础,而不是由法律强制规定必须加人集体管理组织。这一原则与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体现出立法者在制订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方面已经充分认识到,著作权首先是私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也应引进竞争机制。[53]显然,法律并不能直接规定哪项权利直接由集体管理组织行使。
广播权规制范围扩张后,录音制作者的广播获酬权同样获得扩张,不再仅限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音乐的场景。音乐直播直接播放音乐、音乐直播表演唱歌使用原唱伴奏、直播(不限于音乐直播)过程中播放音乐作为背景音乐、网络电台定时播放音乐等均涉及到录音制品互联网广播获酬权。但鉴于录音制品的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一直是由各厂牌与音乐网络平台进行单独授权(例如环球音乐、索尼音乐、华纳音乐与互联网音乐平台均是按期限对海量录音制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单独授权),已经形成稳定有序的授权市场。由此,涉及录音制品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场景,例如网络直播使用、网络电台定时播放歌曲等授权,亦应由各厂牌自行进行许可收费更加合理、高效。如果再引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集协”)介入管理录音制品的非交互传播方式,将可能导致版权重叠、授权不清晰等问题。
此外,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互联网广播获酬权也不应参照音集协管理KTV音乐电视收费工作的形式。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同意以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备组名义开展卡拉OK音乐电视收费工作的复函》[5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音乐电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四条[55],针对KTV音乐电视收费管理,一般是音集协收取作品放映权的许可费用,再向音著协分配词曲表演权相关费用。根据音集协2019年年报显示,音集协将从卡拉OK领域收取的著作权使用费中扣除税金和管理成本后的40%支付给音著协,即6749万元,再由音著协向音乐作品(词、曲)权利人进行分配[56]。部分法官也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当卡拉OK经营者所使用的MV构成类电影作品时,无论其是否经过许可或支付过许可费,词曲作者均不能直接向其主张权利。虽然被使用的MV中涉及词曲作者创作的词、曲,但因其已经融入了类电影作品,使用者使用的也是MV整体,而不是其组成部分,故应由制作者对该MV行使著作权权利。[57]考虑到音集协管理KTV音乐电视具有特殊的行业背景,在录音制品、词曲授权已经形成稳定版权市场秩序的情形下,扩张后的词曲广播权继续由音著协管理、新确立的录音制品广播获酬权由录音制作者自行授权管理更为合理。当然对于广播电台广播录音制品涉及的广播获酬权、录音制品的机械表演获酬权等权利人难以行使的权利,适宜由音集协集体统一管理。
四、 结 语
广播权的扩张合理解决了网络非交互式传播法律定性的问题,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是本次修法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于以直播为主要营收的互联网音乐平台而言,广播权的扩张将加速行业的规范化和资源整合,但广播权扩张后的法律适用、词曲广播权的许可管理、录音制品在互联网领域的广播获酬权的落地实施、集体管理组织对于扩张后广播权的管理等,都将会成为新法实施以后亟需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著作权法实施细则、《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修正、司法解释等进行进一步规范。
注释:
[1]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as amended on September 28, 1979), Article 11bis (1).
[3]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formers,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Rome Convention, 1961), Article 3 (f).
[4]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WPPT), Article 2 (f).
[5]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6] 王迁:《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载《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7] 刘银良:《制度演进视角下我国广播权的范畴》,载《法学》2018年第12期。
[8] 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
[9] 梅术文:《“三网合一”背景下的广播权及其限制》,载《法学》2012年第2期。
[10] 万勇:《<著作权法>传播权修改建议》,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终字第3142号民事判决书。
[1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调查研究》,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16年第2期。
[13] 苏志甫:《从著作权法适用的角度谈对网络实时转播行为的规制》,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8期。
[14] 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184页。
[15] 王迁:《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载《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16] 张伟君:《广播权与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辨析》,载《苏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十三条第(六)项:播放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公开播放作品或者转播该作品的播放,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该作品的播放的权利。
[18] 刘春田、熊文聪:《著作权抑或邻接权——综艺晚会网络直播版权的法理探析》,载《电视研究》2010年第4期。
[19] 刘银良:《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广播权的界限》,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0] 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 Article 8.
[21] 王迁:《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转播”—兼评近期案例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
[22] 崔国斌:《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页。
[2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8号再审民事判决书。
[24] 焦和平:《“机械表演权”的法源澄清与立法完善——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4期。
[25] 姚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26]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27] 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28] 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83页。
[29] 焦和平:《“机械表演权”的法源澄清与立法完善——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4期。
[30]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0页。
[31] 王迁:《论网络环境中表演权的适用——兼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对表演权的定义》,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6期。
[32] [匈]米哈依·菲彻尔:《版权法与因特网》(上),郭寿康、万勇、相靖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33] 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130页。
[34] 王迁:《<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下)》,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2期。
[35] 张伟君:《广播权与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辨析》,载《苏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36] 王迁:《网络主播在直播中演唱歌曲的法律定性》,载《中国版权》2018年第5期。
[37] 梅术文:《“三网合一”背景下的广播权及其限制》,载《法学》2012年第2期。
[38] 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23408号民事判决书。
[39] 艾瑞咨询:《2020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数字篇》,2020年10月,载https://www.iresearch.com.cn/Detail/report?id=3668&isfree=0,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2月20日。
[40]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137号民事判决书。
[41] 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23408号民事判决书。
[42] 熊琦:《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的生成与继受》,载《法学》2013年第12期。
[43] 郭春飞:《浅谈新著作权法对音乐产业的影响》,2020年11月18日,载http://news.zhichanli.com/article/9539.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3月9日。
[44] 王迁:《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转播”——兼评近期案例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
[45]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八条,本条例所称广播电台、电视台是指采编、制作并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机构。
[46]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播放,是指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无线或者有线的方式进行的首播、重播和转播。
[47] 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
[48] 梅术文:《“三网合一”背景下的广播权及其限制》,载《法学》2012年第2期。
[49] 梅术文:《“三网合一”背景下的广播权及其限制》,载《法学》2012年第2期。
[50]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4.08亿!音著协2020年许可收入稳中有升》,2021年1月15日,载http://www.mcsc.com.cn/publicity/trends_67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3月11日。
[51] 许超:《解读<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载《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2期。
[52] 马继超:《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相关问题之探讨》,载《电子知识产权》2011年第9期。
[53] 许超:《解读<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载《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2期。
[54] 《国家版权局关于同意以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备组名义开展卡拉OK音乐电视收费工作的复函》(2006年7月7日 国权[2006]24号),《关于开展卡拉OK音乐电视收费名义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决定,同意你们提出的以“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备组”名义开展卡拉OK音乐电视收费工作的请示。
[5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音乐电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四条,音乐电视制片者与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就音乐作品的使用、报酬支付等有约定,因他人复制、发行、放映相关音乐电视又发生报酬分享等纠纷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可以就合同履行或者侵权向音乐电视的制片者主张权利;音乐电视制片者向复制、发行、放映者主张权利。
[56]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2019年报显示:去年收取著作权使用费2.76亿元》,2020年10月26日,载https://www.chinaxwcb.com/info/567030,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3月12日。
[57] 谢晓俊:《<黄土高坡>等歌曲引发480余起版权官司!词曲作者频诉卡拉OK侵权为哪般?》,2020年6月11日,载http://www.iprchn.com/cipnews/news_content.aspx?newsId=123263,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3月12日。
(图片来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