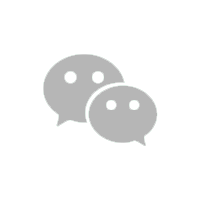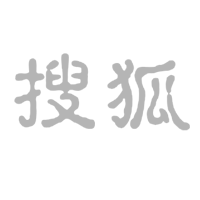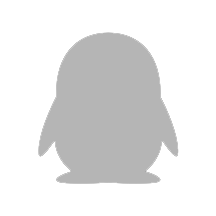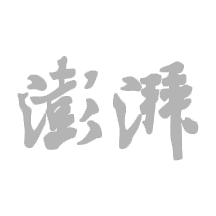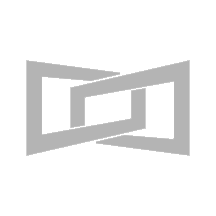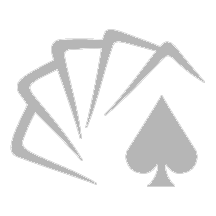天闻说 | 当我们在谈论《游戏主播合同》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作者 | 谢佳佳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本文系知产力获得独家首发的稿件,转载须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并在显要位置注明文章来源。)
(本文5266字,阅读约需10分钟)
在刚刚过去的11月,游戏直播届可谓是“金光闪闪”。11月初,在仁川举办的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上,IG战队以3-0的比分打败FNC战队,一举夺得世界冠军。而在其后几天,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中国王者荣耀第一人”之称的游戏主播“嗨氏”却因违约“跳槽”被判向“原东家”支付四千九百万的高额违约金。在这颇具戏剧性的11月里,我们站上了世界舞台,万众瞩目,而在世界灼热的目光下,投射的不仅是“荣耀”,也有行业乱象带来的“阴影”——各大平台重金“挖角”,热度主播纷纷“出走”,《游戏主播服务合同》(以下简称“《主播合同》”)[1]纠纷频繁上演。
一、合同性质之辨
如今,游戏直播行业已告别了野蛮生长的草莽时代,游戏主播也逐渐的如艺人一般加入经纪公司并与各大平台进行签约。主播方借此获取稳定持久的收入与资源,与之相对的,平台方则要求主播签署“独家服务”条款,以确保主播持续的为平台吸引用户。在不同的主播合同里,主播与平台的商业关系大抵相同,但在法律上的定性却是在“劳动合同”、“委托合同”、“格式合同” 、“无名合同”中莫衷一是。
从主播方的立场来说,主播方多主张“主播合同”在性质上是“劳动合同”或“委托合同”,同时从合同或条款效力的角度论证“主播合同”是平台方基于优势谈判地位拟定的“格式合同”。
在“符亮案”[2]中主播方对“跳槽行为”的抗辩之一便是:“主播合同”为“劳动合同”,但该观点并未被法官支持。法官认为:“从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符亮不受斗鱼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亦不接受斗鱼公司的管理,双方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回归到《劳动法》规定本身,《劳动合同》应当包含的条款有: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置业危害防护等条款,其本质在于双方是否构成隶属于管理关系。《主播合同》在报酬计算方式(约定基本工资与时薪)与绩效考核(约定主播的报酬与观看用户数量挂钩)方面与前述法定条款对应,但主播工作自由的特征更为明显,诸如不固定工作场所与时间,无须遵循特定的员工制度。因此,既有判例中,多认定游戏主播与平台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同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往往将“是否为主播缴纳社保”作为衡量双方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一项重要指标,原因在于这在法官看来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隶属关系”的直接证明[3]。
杭州萧山蓝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诉游戏主播系列案件[4]则让“主播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关联在杭州法院被多次讨论。此类纠纷中,追责方不是平台方而是人力资源公司。这是因为在直播行业刚刚兴起之时,出于税务、风险隔离甚至于便利的考虑,主播合同多由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与主播签订并约定前者委托后者到平台担当主播。合同名称常冠以 “特别委托”字样,同时在内容上明确约定委托事项、委托报酬、禁止转委托等大量以法律概念“委托”表述的合同内容。正是这样的行文方式使得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倾向认定双方构成委托关系并适用委托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5]
除论证合同性质外,主播方另一个“杀手锏”是:“主播合同”为“格式合同”。格式合同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合同。“主播合同”中合作的双方一方是资金雄厚的直播平台,另一方是单枪匹马的个人主播。从平台方的角度,平台方需要发掘无数的主播“潜力股”,因此,“重复使用”与“预先拟定合同”实为业务需要。从双方谈判地位来说,除了头部主播,平台方占据明显优势地位,现实中,平台方无法也不会与主播进行一一协商。因此,主播合同被认定为“格式合同”的概率很高。此外,根据行业现状,游戏主播呈现“低龄化”与“文化程度较低”的特点,法院出于对主播认识能力的照顾,若平台方抗辩合同并非“格式合同”则需负较高举证义务,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此外,即便绕开了“格式合同”的认定,单个条款本身否构成“格式条款”也在多个案件中成为争议的焦点。例如在“裴毅峰案中”法官即认为“协议在明确赋予蓝博公司任意解除权的同时,却限制了裴毅峰单方面要求终止协议的权利。该条款明显存在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当属无效”,最终法官从公平原则出发,认定裴毅峰同样享有任意解除权。
相比主播方各出奇招,平台方作为原告方,观点十分明确:“主播合同”为无名合同。有学者指出:“无名合同,亦称非典型合同,是指法律尚未特别规定,亦未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6]。关于无名合同的适用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明文有载: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民法领域的“类推适用”在合同法上运用的体现。同时,无名合同因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排除了《合同法》分则对具体合同类型的明确限制,当事人之间的意识自治被充分的尊重。具体到“主播合同”,平台方律师多借鉴《艺人经纪合同》相关纠纷的抗辩思路,主张《主播合同》是融合居间、行纪、委托、劳务等多种合同属性的混合合同(即无名合同的一种类型),以此来阻却主播方以委托合同为基础行使“任意解除权”[7]。
二、合同性质不同意味着什么
平台与主播方诉讼之战往往始于“合同性质之辩”而不同性质的合同也意味着不同的抗辩策略。
首先,“劳动合同”可为“缓兵之计”。一方面,《劳动法》第79条规定了“劳动争议仲裁前置规则”[8],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是以已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为前提的。《劳动合同》相关主张的成立意味着主播方可直接避开当前法院审理程序,双方先行进入劳动仲裁的裁决[9]。另一方面,在主播合同约定对合同争议适用仲裁程序的情况下,主播方可以双方构成“劳动关系”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以达到“拖长战线”或争取有利管辖的目的[10]。这是因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劳动争议并非商事仲裁的范畴[11],针对劳动争议适用仲裁程序的相关条款亦无效。
其次,“委托合同”可为 “金蝉脱壳之计” 。《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若“主播合同”被判定为“委托合同”,也就是意味着主播享有“任意解除权”,主播“跳槽”的行为也就变为了正当行使权利,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责性。
当然,即便在法院认定“主播合同”为“委托合同”时,平台方也并不会那么轻易的缴械投降。原因在于,委托合同之“任意解除权”本身就是实务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其一,“任意解除权”背后的法理在于,委托合同成立基础为“信任”,若“信任”丧失,合同亦无存在之必要。前述法理在“无偿委托合同”的情景下依旧是成立的,但对“有偿委托合同”来说,当事人之间依赖的更多是“对价”,主播方希望从平台方获得报酬而平台方希望倚仗主播方吸引用户,因此,“任意解除权”的合理性确实值得商榷。[12]其二,“任意解除权”是否可以通过约定排除,并无定论。在“裴毅峰案”中平台方律师即引用了学者观点认为,“任意解除权”相关规定为“任意性规则”或“赋权规定”,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了委托合同主体该权利,既为权利,合同主体通过合同的约定放弃权利自然也应当被尊重。
最后,格式合同抗辩还可以是违约金“打折券”,与主播最终应当支付的赔偿金息息相关。根据《合同法》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司法实践中,对于主播合同当中包含的违约条款,即便法官认为存在前述无效情形,但从整个行业发展角度出发,法官也并不倾向从根本上否定条款的效力,更多的是从作出对提供方不利解释的角度着手,限定违约金的范围。在“刘洋案” 中,合同约定违约金的金额为“年报酬”的三倍,因此关于“年报酬”范围的认定直接关乎违约金金额的高低。平台方认为“年报酬”是指主播方实际获得的报酬而主播方则主张“年报酬”仅指合同约定的固定收入。而最终法院认为“违约条款”构成格式条款,因此若双方发生分歧,应作出不利于平台方的解释,故而支持了主播方的主张,最终判定主播方支付三万六的违约金,这一数额与原告主张的三十万,便相去甚远。
三、知道了这么多道理,我们能否写好“主播服务合同”
合同好比企业的“防弹衣”,“闭门造车”时也许我们没办法精准的预测枪林弹雨会从什么方向袭来,但起码经历了几场战争后,我们可以知道当前需要在什么地方对我们的“防弹衣”进行缝补加固。笔者认为,从平台方的角度,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签约主体的角度来说,尽量避免以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与主播签订合的方式与主播建立合作关系,以规避主播合同被认定为“委托合同”的风险。平台方可选择直接与主播、直播的经纪公司,甚至于主播、经纪公司、三方的方式签订主播合同。具体说来,首先对于头部主播来说,建议直接与主播或者与主播及其经纪公司签约。从合同相对性的角度出发,若平台希望能够对主播直接发生控制力,让主播个人直接作为签约主体进行签约是最恰当的方式。而如果在主播已加入经纪公司的情况下,也应当将经纪公司纳入签约主体。理由在于,一方面,可以要求经纪公司对主播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经纪公司本身也意味着良好的缔约能力,降低了“主播合同”被认定为“格式合同”的可能性[13]。其次,对于一些新生潜力主播,让平台与之主播个人一一洽谈签订协议,实践中实难做到,因此若从效率出发,平台方选择与拥有大量新生潜力主播独家经纪权的经纪公司签约,由经纪公司负责主播管理,也不是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折衷之策。
第二,从采用的合同版本与样式角度来说,注重体现“差异化”与“个性化”。首先,可以根据签约时知名度(例如是初出茅庐的潜力股还是已有一定用户基数的成熟主播),拟服务年限(是准备试水合作几个月还是长达数年的长期合作),甚至于主播自身因素(年龄、是否为在校学生)等不同情况尽量多的拟定不同版本。此外,在格式上避免选用 “通用条款与特别条款”的格式或“设定完备的格式条款,并在特定部位空出几行”的方式。
第三,从合同具体的内容来说,首先,避免使用“委托关系”“劳动关系”及其相关字样,同时建议明确添加宣示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委托关系”条款。其次,注重条款的相对平等,若条款的设计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法官极有可能认为这是显失公平的格式条款,因此作出对平台方的不利判决。此外,尽量避免在合同中约定为主播方缴纳社保、要求主播方在固定时间到固定地点进行直播等明显具有“劳动合同”色彩的条款。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固定双方对合同进行磋商的过程。可以采用书面认可、语音、甚至于录像的方式对双方协商过程进行记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请专业人士就重要条款的含义向主播方进行说明以避免日后主播方以对合同内容不理解或合同内容未经磋商等理由进行抗辩。更重要的是,定期管理与更新合同。根据主播商业价值适时调整合同内容,或者变更签约主体(如前所述,对于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主播,应当将主播作为直接的缔约主体以落实权利义务)。若涉及为主播花费大额费用,平台方应及时签订补充协议,将该部分费用计入主播收益或以其他方式记入直播解约应当支付的违约金。[14]
注释:
[1] 游戏主播行业为新兴行业,平台与主播之前签订的合同并无统一的名称,本文姑且以《游戏主播服务合同》指带此类合同。
[2] (2016)鄂0192民初3602号
[3]“鲁大棒案”:(2016)浙0106民初8119号;(2017)浙01民终2153号;(2017)浙民申2534号
[4] 如“鲁大棒案”,“裴毅峰案”:(2016)浙0106民初9660号,(2017)浙01民终7346号
[5] “裴毅峰案”:(2016)浙0106民初9660号;(2017)浙01民终7346号
[6] 《合同法总论》(第三版),韩世远,p48,法律出版社
[7] “裴毅峰案”:(2016)浙0106民初9660号;(2017)浙01民终7346号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 “符亮案”:(2016)鄂0192民初3602号
[10] “唐磊案”:(2017)粤民再403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12]“裴毅峰案”:(2016)浙0106民初9660号;(2017)浙01民终7346号
[13] “嗨氏案”
[14] 在“嗨氏案“中,原告2016年9月签约时,违约金为300万,2017年1月签订的协议约定违约金为2400万或者所得收益的5倍。此外,还与嗨氏签订了《高能少年团》合作之补充协议,将平台资源投资折算成具体的数字记入了嗨氏的收入,进而成为了之后嗨氏违约金计算基数的一部分。